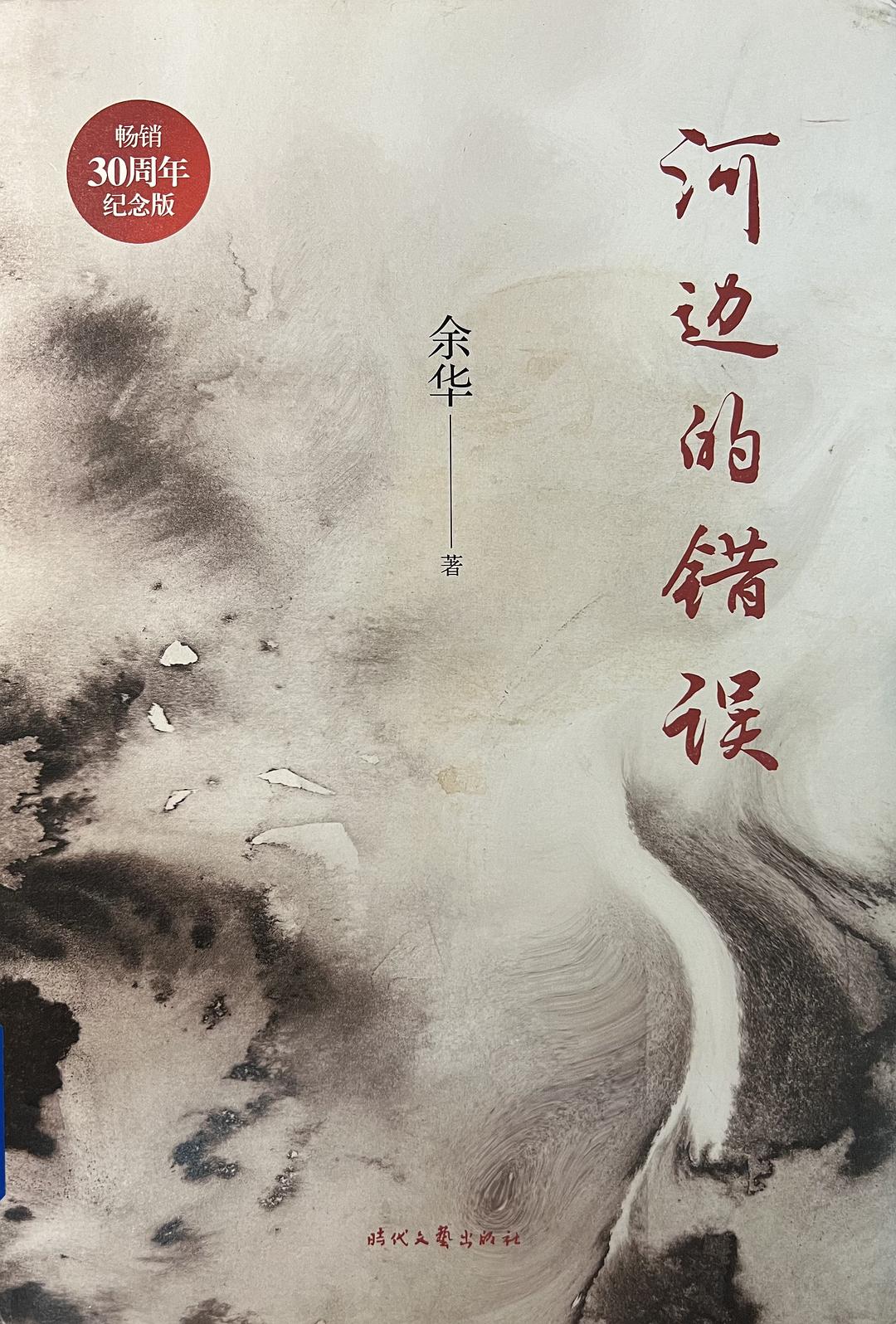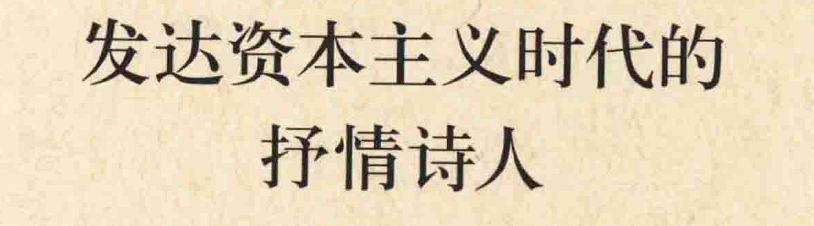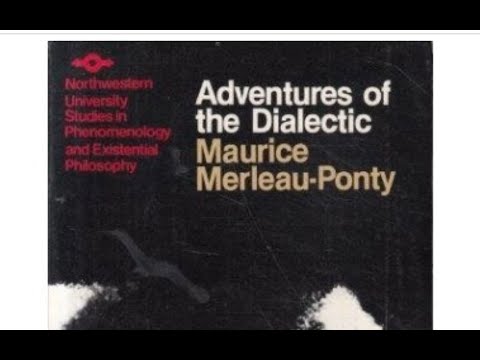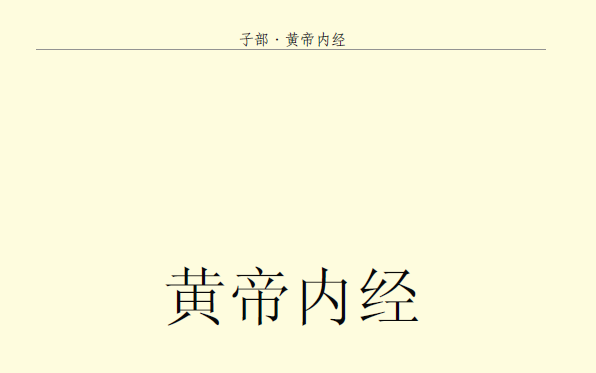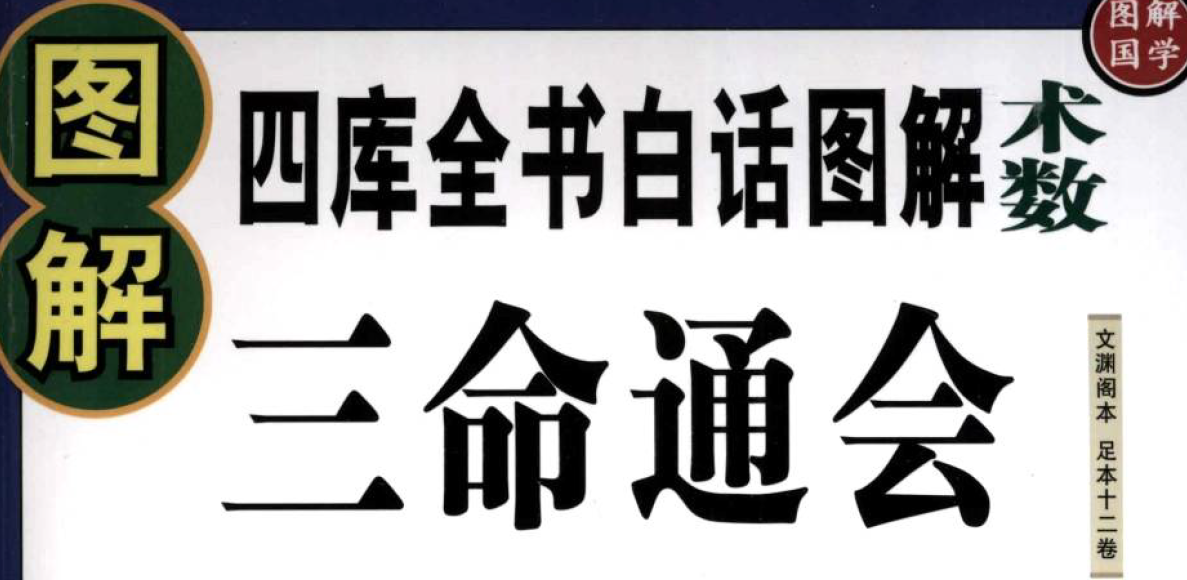从一个小游戏讲起
从一个小游戏讲起
Ivoripuion我们可以设想这么一个游戏:在黑板上随意写一些数字,比如0、1、2,然后让人在黑板上写一个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数字。这时悖论发生了:当一个“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数字”铭刻在黑板上的那一刻(比如“3”),这个数字就已经不再是“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数字”了。
这个悖论更加通俗的说法即理发师悖论:
小城里的理发师放出豪言:他要为城里人刮胡子,而且一定只要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但问题是:理发师该为自己刮胡子吗?如果他为自己刮胡子,那么按照他的豪言「只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他不应该为自己刮胡子;但如果他不为自己刮胡子,同样按照他的豪言「一定要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他又应该为自己刮胡子。
该悖论的集合论版本便是“罗素悖论”:将所有不是自身元素的集合构成一个集合A,即A={x:x∉x},此时似乎很难说明A∈A或者A∉A。一个更通俗的例子为:A:{A....Z},当A代表一个包含所有大写字母的集合,那么A到底在不在这个集合中是难以说清的。该悖论后续由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施打了个补丁解决:任何函数都不能包含自身。维特根施坦的这种解决方法也不难得到《逻辑哲学论》的命题七: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就必须保持沉默。在完全排除主体来获得一种纯粹的语言以及“纯粹书写”后,维特根施坦试图在经验世界(事态)的角度获得数理逻辑上的真理——话语本身就宣示的真理。
精神分析也因此比数理逻辑走的更远。在A:{A....Z}这样的集合悖论中,精神分析将A定义为一个由被排除的主体叙述出来的概念,这样就不会参与到集合的包含关系中(这里与维特根施坦类似),而被排除的部分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无意识的向度,精神分析在此与维特根施坦的“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以说的都必须保持沉默”的姿态是完全不同的。和认可笛卡尔主体的康德的不可知论类似,晚期维特根施坦也不得不走向神秘主义。
我能够想象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畏”意指什么。人具有冲破语言界限的内在冲动,想想,譬如对任何东西存在所产生的惊讶,这种惊讶不能以一个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对它也没有任何答案,我们欲说的一切都先天地要成为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们总还是力图冲破意义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 《论海德格尔》 何卫平译 邓晓芒校
回到开头的小游戏,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数字”这样荒谬的情况呢?因为有一个叙述“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最小整数”的叙述者,这个出了这道题目却又没有参与书写行为中的叙述者就是一个不在场的大他者,大他者以自己的匮乏划出了边界产生了宇集合。
主体的自我认同,便是从大他者这个宇集合中划出一部分然后指示出来,这样的方法也必定与大他者一样是存在欠缺的。大他者作为能指的宝库是(Sa,Sb,Sc,....),将其中的某些能指指定为主体S1,那么代表这些个能指组合的能指S2就一定在这个能指宝库之外,否则就构成了罗素悖论。这些被排除的能指,就是“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
既然真理始终只是一半的真理,那么真理还有何种可能?
在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宇集合中,无产阶级作为阿甘本口中的“神圣人”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个被排除的阶级正是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集合的能指,换言之,无产阶级作为真理奠基了社会。正如“人并非没有真理”,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没有无产阶级,只是资本主义结构的主人话语将劳动贬黜引入货币、将商品的使用价值排除用交换价值代替;也正如“真理就在于‘欲望以其欠缺所掩饰之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就在于它竭尽全力排除、掩盖的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异化的劳动。
主人话语的排除作用于生活便可见一斑:没有身份的三和大神、没有实质权力的工农群众、甚至于曾经是(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被从(小)资产阶级排除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些事实都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崩溃的极端条件下,许多的人都成为了本雅明口中的游荡者,而事实的被掩盖也正暗示了大他者的匮乏,这种匮乏也只能通过符号性的否定来遮盖。资本主义匮乏的最一般表现就是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
无产阶级在主人话语的统治下聚合为城市中的人群,在与市场符号化商品类似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符号化无产阶级,这种符号化实则正是一种排除作用——将无产阶级的能指排除,以其余的什么能指代替,诸如LGBT、女权主义等。这种遮盖又在超我欲望的二重性中不断地将无产积极的特质显露,激发揭露大他者匮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