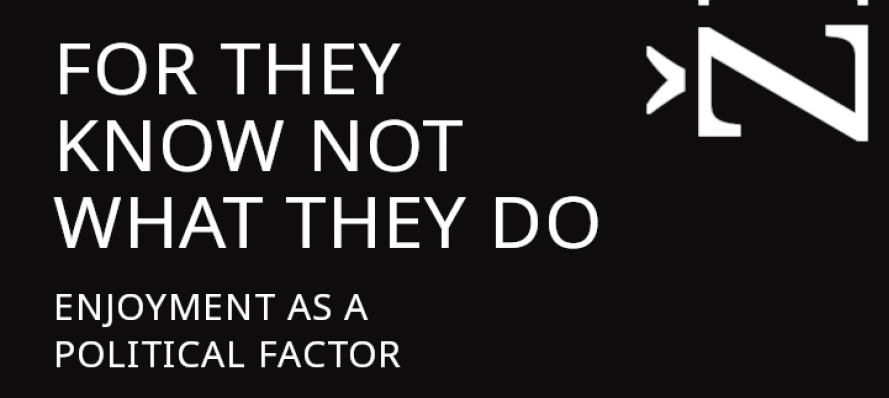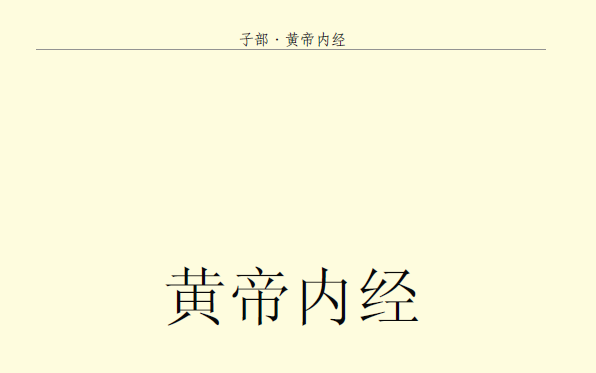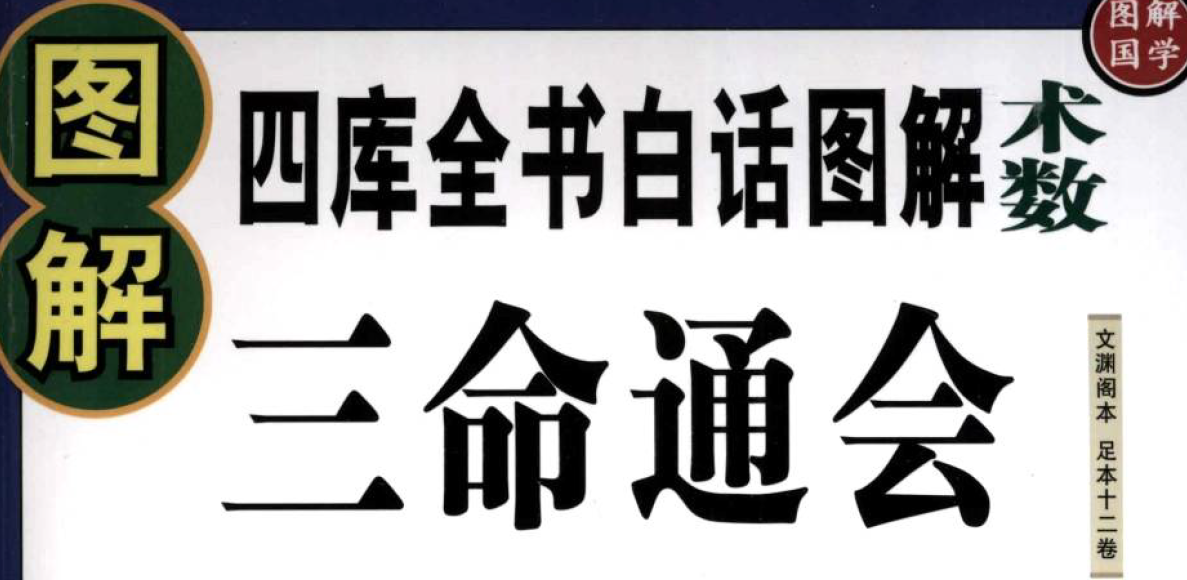《红豆》陶云潜——三重创伤下的主体性回归
《红豆》陶云潜——三重创伤下的主体性回归
Ivoripuion《红豆》陶云潜——三重创伤下的主体性回归
对精神分析而言,《红豆》中的三子陶云潜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童年时期的和兄长的二元欲望关系,兄长战死后的第一重创伤、简望舒道明心声后的二重创伤、白思尧死亡后的三重创伤的相互作用。对陶云潜而言,根本性的创伤仍旧是兄长死亡的第一重创伤,并且在关键的二重创伤和重放式的三重创伤后,陶云潜的欲望与大他者的欲望彻底分离开,得到主体性的回归。
陶云潜作为陶家的三子,自小个体的欲望就被国尔忘家这样的宏大叙事所代替,这是他一直承担着的大他者;他的兄长陶云疏一直扮演着他的母亲角色,通过两者的相互欲望,陶云潜获得了自己的在想象界的完整性。
云潜首先遭遇的激烈冲突是兄长的为国捐躯——大他者将云潜从他和兄长的二元欲望关系中强行分离开了,但是结果怎么样,云潜的欲望真的和大他者欲望分离了吗?可以看到,云潜继承了兄长的遗志,他的欲望中心仍旧是大他者的欲望中心——国尔忘家。他的母亲能指——兄长的死亡,让他清楚意识到了象征秩序的存在,但是他没有将大他者在他身上的欲望(欲望他能投笔从戎)和自己的欲望(从事文艺事业)分离,而是将大他者欲望在事件后完全取代了自己的欲望。此时,云潜就陷入了经典的抑郁症的矛盾中——主体通过欲望转移将自己的自我认同于丧失的对象,将幻想的丧失回转到自身上来。这也不难解释,他在替兄从军初期一直保持自己的整洁状态——此时他将兄长的欲望丧失转移成了自恋。
兄长的死亡对于云潜来说是首次创伤,这次创伤对他来说的却是在其遭遇的第二次创伤后才能被意识到的。
简望舒的出现是一个关键的桥段,在望舒出现之前,陶云潜都是家中最小的三子,他都是被享乐的对象,他的欲望都是被潜抑的,他的兄长扮演了母亲能指的大他者,而姐姐也能揭开自己的女性面纱成为享乐的获取者。简望舒的出现,让云潜意识到有一个更加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且恰逢兄长死亡,简望舒成为了他对之前丧失的补偿,他将自恋的移情完美的转移到了对这个小妹的爱恋上去。此时有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也就是望舒告诉云潜,她要去做一个电报员,为国家效力,这个关键的节点也让云潜内心深刻触动——原来,望舒也是象征秩序的的一部分,而非想象界的互相欲望的对象。望舒身上的那个无法解释的部分(她身上那朦胧的与兄长的相似感),终于在这个节点后让云潜深刻意识到了本质性创伤——实在界总有无法解释的爱,这种爱一如他对兄长的爱,不断地逃离着他。后面我们也能看到,云潜对望舒的爱是如何让云潜自己的主体性得到回归的。
第三重创伤来自于白思尧的死亡。白思尧在陶云潜的兄长陶云疏死后一直扮演着他的兄长的角色,虽然云潜本人并不认可这个“兄长”,因为相比于陶云疏,白思尧扮演的更像是一个“原父”的角色——他夺走了他的二姐,夺走了亲生父母的关心,以至他的全部享乐似乎都被白思尧夺走了。直到白思尧死亡的前一刻,我们都可以说陶云潜并不认可白思尧,但是白思尧为了陶云潜和望舒而操纵飞机撞向敌军的那一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白思尧这个姐夫的死和陶云疏的死亡是出奇一致的,都是在大他者的欲望下,以军人的身份赴死;但是白思尧和陶云疏的死又是不一样的,因为白思尧的事件中,有一个简望舒。前面已经说过,简望舒让陶云潜意识到了本质性的创伤,而为了弥补这种创伤,陶云潜不得不将简望舒的大他者身份转化为自己的小a,成为自己的欲望对象。白思尧为了简望舒和陶云潜而死,终于让陶云潜意识到了大他者欲望和自己欲望的矛盾性,自己的欲望是由大他者欲望的残余塑造的,但是自己的欲望终究是需要和大他者欲望分离开的,对云潜而言,这个分离的实践就是去追求与望舒的恋爱关系。这个恋爱是如此违抗大他者的意志:一方面云潜不得不放弃自己“国尔忘家”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望舒又是云潜名义上的妹妹,这样的恋爱是绝对禁忌的恋爱。
陶云潜在台湾写了1478封信给简望舒,虽然没有一封寄到了望舒那里。云潜终究在三重创伤后意识到了本己的欲望,在欲望的闪烁中,云潜找到了自己的本己主体性。
在陶云潜终于找到了自己后,却因为时事的因素而没有成功完成自己与望舒的恋爱关系,这也是这个故事根本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