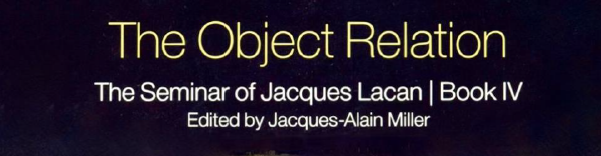三年小结
三年小结
Ivoripuion正如分段的阶梯必须通过分割的上一段来证明当前处于阶梯的顶部,我也只有在对过去三年的经历画上句号才会写出“三年小结”这样的题目——这也是我近些时间来最大的感受,似乎只有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庸庸碌碌的作为常人的我才会发现以往日常生活中的事或人的珍贵:这件事情若是不做也许以后就没机会再做了、这个人若是不见也许以后就没机会再见了。这种对将来的否定、对可能性的否定恰恰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不可能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边界),在这种极端可能性的威逼下,我才会去探索日常生活中那些的可能性,而我过去往往会选择性地忽略掉这些可能性以便于自我的稳定性。这里的稳定性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仅是我们想象的、象征的关系网,比如与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等,也是我们的存在之域,它包含了我们的身体、作为环境的母体、熟悉的面庞、亲切的声音等。基于想象,在存在之域中我们收获了一种有根的错觉,背向了“无何有之乡”的痛苦,得到了自我认同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离别也可以理解为对欲望回路的彻底癔症化。癔症结构对欲望满足进行限制,离别是对于欲望满足的彻底否定:那些未发生的事件以后也许就不可能再发生,现在构造好的存在之域以后就土崩瓦解了,那些面容、声音、气味以后就从你的周围世界中消失了。离别之人因此就变成了客体,他作为主动发起的送别方最后在自反性中变成了被送别方,即便在这种的癔症化逻辑里他无法真正做到送别自己。在飞机飞离宝安机场的那一刻,我心里没由来冒出一句“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深圳了”——既然我做不到送别自己,就将引发自反性后藏起来的想象自我留在想象的深圳了。
那我想象的深圳是怎样的深圳呢?在我第一次从江苏坐火车到达深圳的那一天早上偶遇一个穿了婚纱的白毛coser时我对深圳的想象就已经奠定了:深圳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城市。此后我加入腾讯结识了更多有趣的同龄人,以朋友建构的想象关系让我安全地保持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最初想象。当然想象关系是安全也是不稳定的,它总是被象征关系决定,就比如当我面对家里老人的疾病、即将到来的工资降低等状况,我不得不走出这种想象的安全居所,重新审视我的存在之域。
21年到24年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周围世界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于个人工作来说,我从专精于二进制漏洞分析转向了web安全,于个人精神状况来说,我因为大学毕业时的一些事情彻底开始厌恶自己曾经的强迫神经症结构,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我身处的社会来说,我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后社的氛围。什么叫“后-”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辩证法的庸俗三段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发现根本分裂后自己无能为力后还是要去做,这也是我目前为止找到并试图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聊天,总是在骂着社会一些现状后转身又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就好像大他者无能我们早知道,但是我们还需要它去维持象征界一样,我们总是在心知肚明地互相欺骗。
当我到家时已经是深夜,正如四年前我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一样,但那时候心境和这次的心境截然不同,四年前强迫而不自知的我总是想着无限的可能、追求着作为界限的事情,现在我依旧保持着这样的可能性,不过这是在发现可能性是被不可能性包裹着后的坚定立场,正如当我在飞机飞离深圳时内心说的一句“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深圳了”其实是一个问句,这个问句的我的第一个答案由在场的自我给出——“不可能”,而另一个答案已经同时由不在场的言说的我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