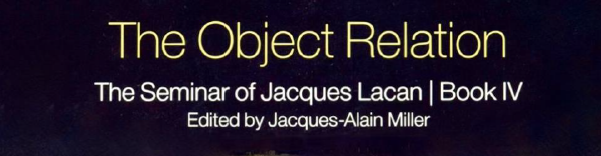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一个救世主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一个救世主
Ivoripuion海德格尔将“常人”定义为此在操劳着消散于世的非本真状态,而要从非本真通往其所谓的本真状态就需要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见证,即决心:向来因为落后于自己的可能性而有罪责的此在终于在良知的评判声中回到了曾经背离着闪避的本真能在面前。处于“不之状态”的罪责能在,在终极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死亡面前,回到了自身,这也所谓的“向死而在”。这样的思路也能与一般的流俗的“觉醒”的概念一致:我们在遭遇到一个外界的入侵后终于发现自己的原来的问题,然后不断改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这样的观点下,所有的“常人”就都在等待着一个拥有“天命”的人去带领着去抵达本真的领域,这个拥有“天命”的人在遇到所在的社会遇到危机后第一个“觉醒”。
不妨以一种集合论的方式去看待海德格尔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这时它是一种纯粹否定。个体的被确立首先就是一种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我是我”——自我设定自我本身,而自我设定自我本身是基于我的一个空位,也就是自我设定非我。正如黑格尔的“God is God”,“God”作为一个全集在“is”这个系词的作用下期待一个更具体的子集合的谓词来具体化自己,但是它遭遇了是“God”这样的同义反复,于是“God”首先遭遇的是“全集减去全集”也就是一个空集,这个空集作为全集的子集也就是拉康所谓的多出来的空缺。简单来说,个体能够被指称出来,是基于其分裂出来的否定对立面。
用拉康的方法解读海氏的常人的“向死而在”,将庸庸碌碌的常人以能指链中滑动的能指比较,那个其领导作用的天命以主人能指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熟悉的概念了:常人要能从沉沦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就必须树立一个具备否定性的天命,这个天命也就是前文说的多出来的空集。用佛教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分裂的自身否定,其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就是大乘佛教有关菩萨的悖论。菩萨是觉悟的人,可以涅槃,但实际上菩萨无法一个人涅槃的:若菩萨自私地涅槃,那么他所在境界就不是菩萨;反之若他不自私,他当然不能涅槃。因此没有人可以涅槃:我们不能涅槃因为我们不是菩萨,而菩萨不能涅槃是因为他是一个菩萨。显然,在这样的悖论下,救世主不可能被等出来,常人在等待天命,而天命在等待常人。想摆脱这个死循环的方式就是树立一个自私的人,他能将错误的世界丢弃——不如说他就是这个错误的世界,这也是道教羽化和佛教涅盘的差异。
那既然自我认同产生的主体本身就是分裂的,那还需要这个天命吗?那个非我不就是自己的天命?主体向来就已经拥有了解放自己的那个空集。真正的决定时刻也并非是外界干预而是自我的反思,也就是“A是A”这个命题中那个“期待性”的间隙——期待一个谓词结果得到了自身,于是产生了反思。主体也并不需要救世主来解放自己,自己就可以完全地解放自己,我想,这也是“救世主”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