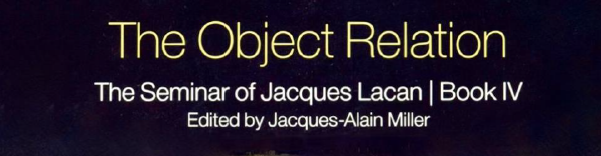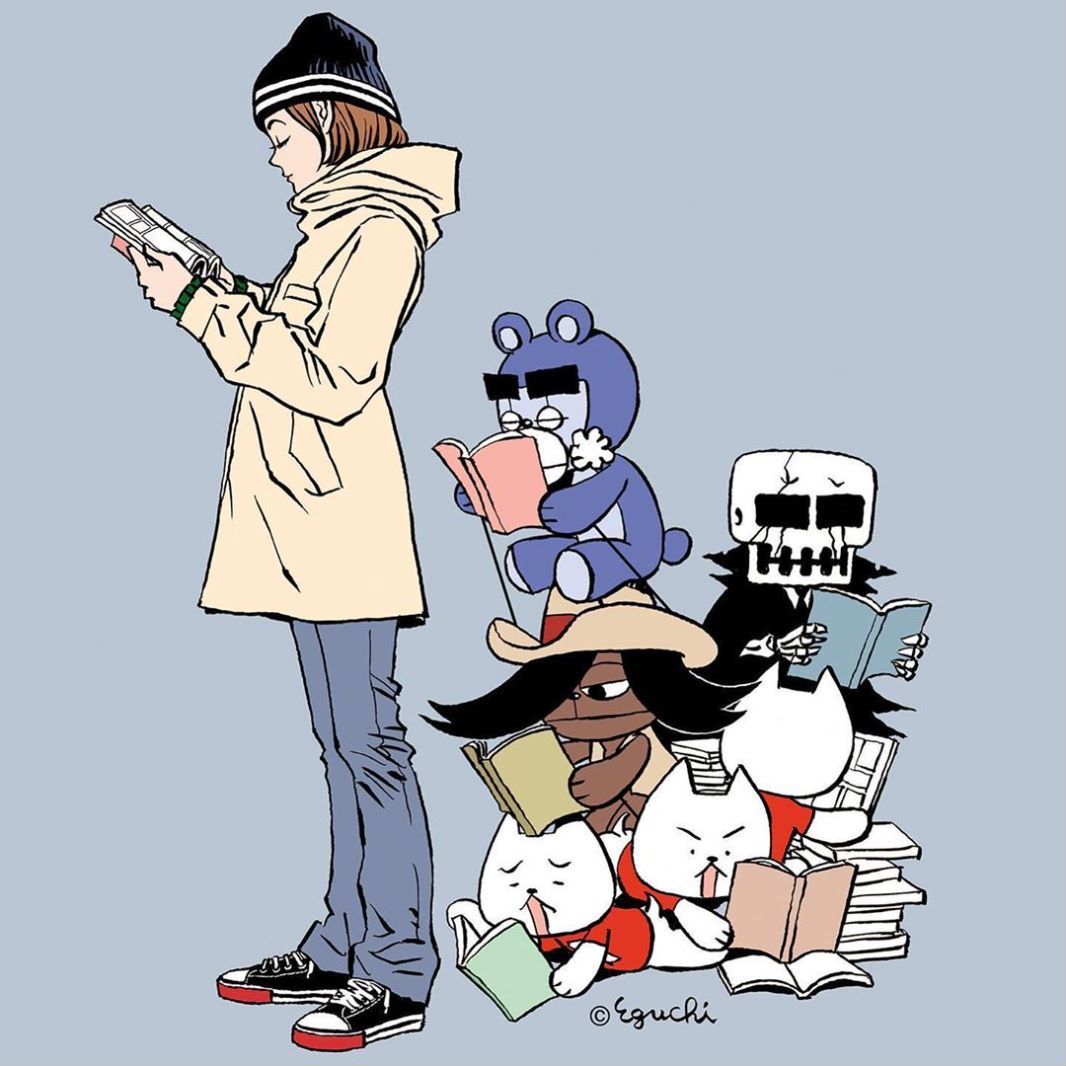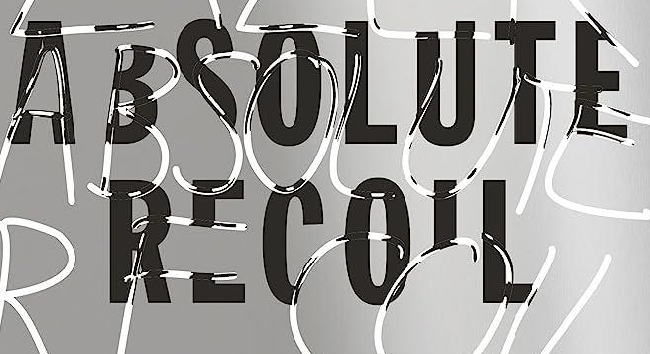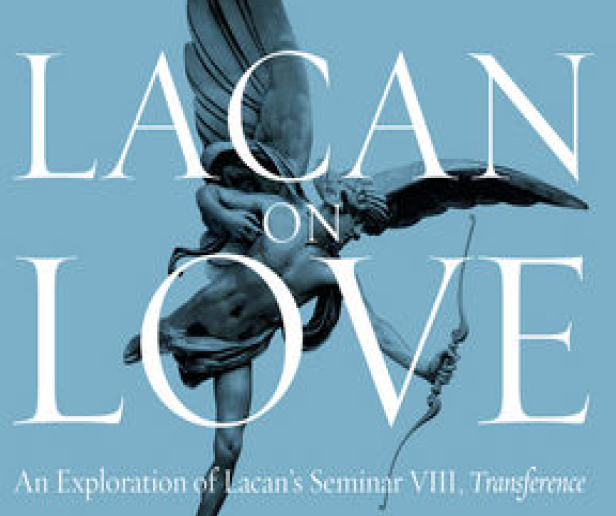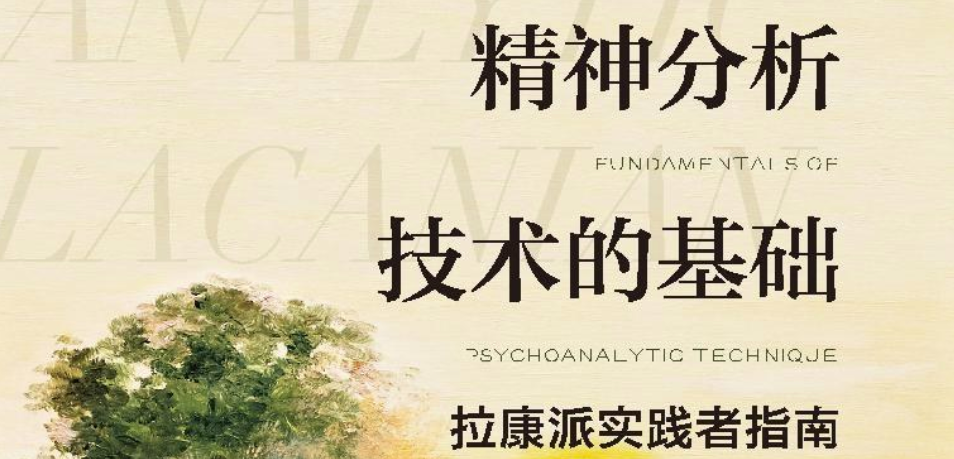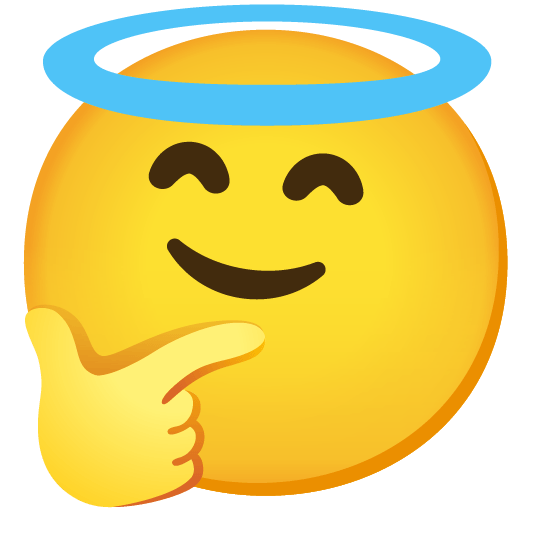导读1-5第一部分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客体缺失的理论化”:
什么是缺失的客体;
三种类型的缺失以及它们的发展性展开;
“恐惧症”和“恋物癖”中缺失的客体;
客体关系理论的人的思想:童年早期的经历会导致一个人的最初照顾者的形象内化,这个内化的形象就是客体,而内化的往往是局部的,也就是部分客体。同时部分的客体会在某一时刻整合,形成好的/坏的他者。
这里的客体和和主体区分的客体不同,只是一个心理表征,是和主体关系在一起的。
拉康质疑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几个点:
这些客体关系理论家强加于弗洛伊德的生物学解释;
对客体的整体概念提出了异议,无论它是关于婴儿期的某种和谐概念,还是对于客体的剥夺或饱和所带来的挫折感的过分强调;
重要的并非是客体,而是客体的缺失。客体的缺失和童年的满足感相关,会激发人们通过一种不可能的重复来重新发现该客体,分析就是关注寻找的东西和发现的东西之间的空隙。
然后寻找的东西,其实就是现实原则下起作用的客体:通过现实原则产生的客体是起面具作用的客体,用来抵挡在主体世界背景中运作的原初焦虑。
三种类型的缺失:
挫折:想象界的损害,缺乏一个实在的、原初的客体,造成缺失的是象征 ...
爱的一种定义是“爱是给予你所没有的东西”,人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往往是将东西在所指的层面上进行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就体现他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依然会选择花时间来陪伴孩子——时间成了切实的缺失的东西,爱成了可以直观得到的现象。又或者,恋人说“我把我的心都给你”,似乎心是一个可交易的实在,而爱是通过牺牲换来的客体。
但当拉康在第八期研讨班说出“爱是给予你所没有的东西”之时,这个“东西”指向的是向来不在场的缺失,爱诞生于对这种缺失的弥合性尝试——爱是象征界回溯性生产功能下对实在界剩余施行的幻想性补充。
在俄狄浦斯第一阶段,孩子在第一次向母亲提出要求(demand)来满足自己的需求(need)并得到母亲的“一划”式回应时,实在界的剩余就已经产生了:需求只能被意指化后以要求的形式表达,而意指化过程必然使其发生异化。母亲的回应——无论是否及时、充分,都无法触及被象征秩序排除的创伤内核。挫折(frustration,也在《永夜微光》译作“欲求不满”)并非源于母亲的偶然缺席,而是因为语言对需求的异化:一旦需求转化为对他者的要求,它就注定产生剩余。正是这一剩余,构成了欲望的起点,也为后续“爱”的幻想提供了必要条件 ...
语法混淆漏洞:指系统中的两个或多个组件因语法规则的模糊或不一致而以不同方式解释同一输入时所发生的现象。
文件上传漏洞的经典案例在 HTML 表单中上传文件时,即enctype="multipart/form-data"的请求中,上传文件通常包含如下字段:
1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 filename="example.txt"
为了支持非 ASCII 的字符,filename参数也可以表示为:
1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 filename*=UTF-8''example%2Etxt
在这里,filename*=UTF-8''example%2Etxt和filename="example.txt"是等价的:
filename*:扩展参数名。
UTF-8’’:表示字符编码为 UTF-8,语言标签为空。
%2E:URL 编码的点号 ...
导言“毫无疑问这里有块骨头”列宁引用的恩格斯的主张:唯物主义会随着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而改变其形式。因此对恩格斯唯物主义的修正并非“修正主义”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绝对反冲的概念黑格尔用过一次,在运动中对立的思辨统一下,事物从自己的丧失中涌现。
当设定性被自我扬弃时,本质不再直接由外部的大他者决定,而是通过与其自身他性,以及它同它所涌现而出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复杂集合所决定。
事物是自身内部对自身的绝对反冲。
本书结构:
第一部分:对两个具有非先验性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阿尔都塞,巴迪欧)进行批判性分析。
第二部分:论述黑格尔式的绝对(AbsoluteAbsolute)。
第三部分:黑格尔式的探索,到达超越黑格尔的神秘地带。
旧与新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四个版本:
还原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认知主义、新达尔文主义)
强烈批判宗教的无神论新浪潮(希钦斯、道金斯等人)
话语唯物主义”的任何残余(福柯式的对话语物质实践的分析)
德勒兹式的“新唯物主义”:物质=生命=能动自我意识流
弗兰克·鲁达: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
观念论强调了我们身体有限性的同时,努力 ...
导言爱是开端祖师爷弗洛伊德就是通过分析他的一个女性病人的转移之爱发现这些情感能够被利用并使其作为治疗过程中的发动力。
爱的抱怨一部分人对于灵魂伴侣的追求实则就是追求一个完美的镜像,一部分人追求的是一种一见钟情式的着迷。
言语,言语,言语拉康口中的爱含义是多样的,他往往会将爱和欲望混淆起来。
本书的脉络:
象征界;
想象界;
实在界;
诸多哲学家对爱的思考;
第八期研讨班的一些讨论;
象征弗洛伊德式的开端:爱情三角爱情中的强迫症患者弗洛伊德:有一种男人必须在有另一个在他出现之前就已和(他喜欢的)女人有关系的男人感到嫉妒或是对其有一种“竞争和敌意带来的悦人的冲动”下才会进入爱情,即他无法爱上一个没有早已与其他男人有染的女人。
这是因为,强迫症本身追求的就是对不可能的欲望,只有在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第三方来中介,使得他的追求无法实现,他才能去追求与女人的关系。
强迫症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幻想这个第三方中介的象征身份地合法性,由此才让这个三方中介成为一个父亲一样的对手。
强迫症的分裂:
意识:另一男人的女人吸引了他;
无意识:与另一男人的战斗使他着迷。
爱情中的癔症患者弗洛伊德:有一些女人 ...
通俗理解的“服美役”即“女性为了符合社会主流的‘美’的标准,而投入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进行各种美容、瘦身、医美等行为”也许可以从《规训与惩罚》中引出,即社会中对于女性身体标准的需求的共识实则是为了更好的惩罚,得以让个体被裹挟进集体中,将惩罚的权力更深入地嵌入社会的集体。在这种语境下,“美”是一种标准,它的制定者/观察者毫无疑问是大他者,“美”被拘禁在了象征界,成为了“役”。
但是,“个人的生活就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一幢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自我理性的构建完成后,美的定义正如判断力批判所说的一般,既是客观的,亦是主观的,而在主观的层面上,对实在身体的修饰恰恰让个体成为了“当下即是”——它总是拥有着可能性,而非现成。化妆作为”当下即是”的瞬间,使女性从现成的、被规定的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不断生成的存在可能中。化妆在此成为了最小的政治,女性通过化妆这种自我技术进行对身体主权的争夺,收获了倒错式的享乐——这场主权争夺注定失败,因为“成功”的维度总是不在场,父之名下的资本主义总是在囫囵吞枣,它吸纳着一切——包括化妆、亦包括“不服美役”,然后排泄 ...
倾听与听见我们通常的倾听方式忽视或者拒绝了他人的相异性,换言之,我们的倾听有立场/预设/偏见/习惯性地用之前的经验去理解。分析家也不能屈从于共情,因为这些共情反而往往适得其反。
表达共情地技巧:分析者给了一个艰难处境,分析家可以要么给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神情,要么回复一个温暖的“嗯”。
分析家能“真实”了解分析者的诉说的前提,往往是分析家不再将分析者的境遇与自己的对比。
上述的这些倾听都是在想象界上的倾听——试图去听出其中的“意思”,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与分析家“ego”无关的都会被忽略掉——含糊不清、结巴、咕哝、引起误解的言说、首音互换、停顿、口误、模棱两可的措辞、词语误用、双关语等等都被忽略了。
分析家在想象的模式中运作得越多,她能听到的就越少。
推迟理解分析家必须对分析者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兴趣,用对分析者来说未知的方式去关注/理解分析者的言说。
分析家也不能明显表现出对分析者言说的怀疑,否则会导致分析者的逃走——去找一个他那边的人,而是要逐渐的进入一种抛出对分析者言说的怀疑的状态。
倾听需要暗示我们正在专心听,而不需要暗示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所 ...
对杨景媛事件的主要批判会将其包装为“辱女狂欢”,批判者们认为在法律和规范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对女性侮辱的秘辛,并通过假设“想必侮辱”的男性“主动式被动”地陷入同样的“侮辱”之中——批判者幻想中的男性网民,因为主动享受着倒错式的集体意淫而被动完成了辱女行为。在这悖论性的批判之下,幻想通过“辱女”这个主人能指化的伪造地基建造起整个叙事高楼,试图将学术不端、亲人离世、污蔑控诉等所有的创伤吞噬——毕竟,还有什么比将一切苦难都转译为性别叙事,更能完美遮蔽父姓机器无能的哀嚎?当遮蔽完成,象征秩序便再一次完成了系统升级,批判者成为了真正辱女者——自然也是最忠诚的父权主义者。
杨景媛事件是破碎的:伪造《离婚法》的学术欺诈、将“湿疹”误认为是性骚扰、败诉后对肖同学“追杀到天涯海角”的宣言等都是偶然突发的。但是当伪女权主义者将这些事件缝合到“父权压迫女性”的宏大叙事时,真实而突兀的事件被回溯性异化为连贯的历史,杨景媛事件也因此产生了其同一性的“自我”——“辱女狂欢”。而武汉大学的沉默、相关人员的上门警告等接连发生,更是将破碎的历史在主人话语进一步弥合,产生了其“自我理想”,杨景媛事件成为被父姓机器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