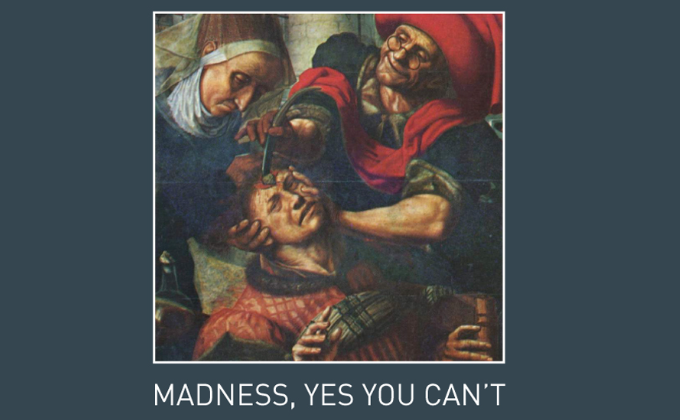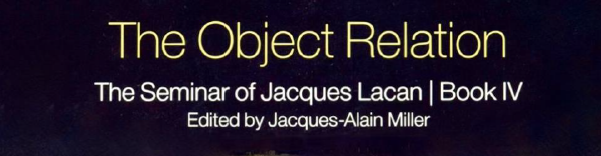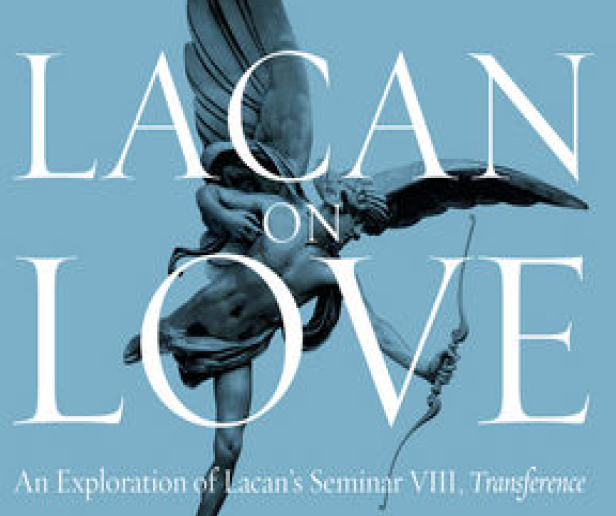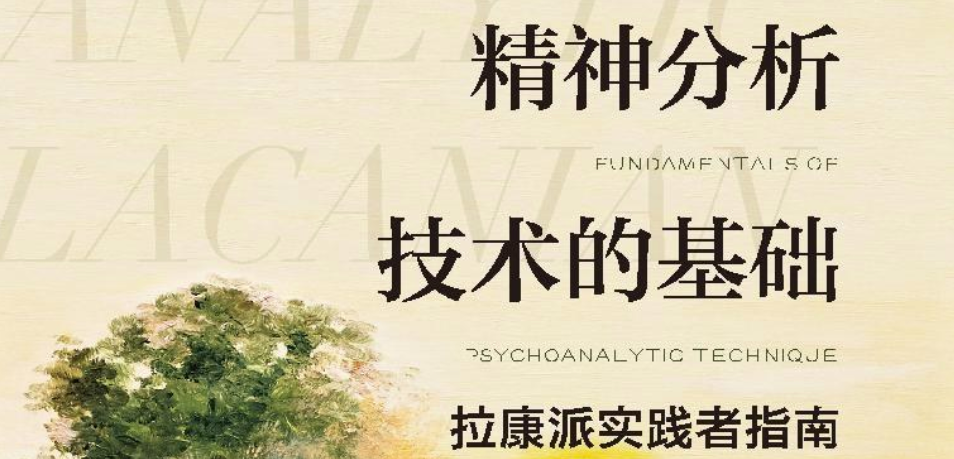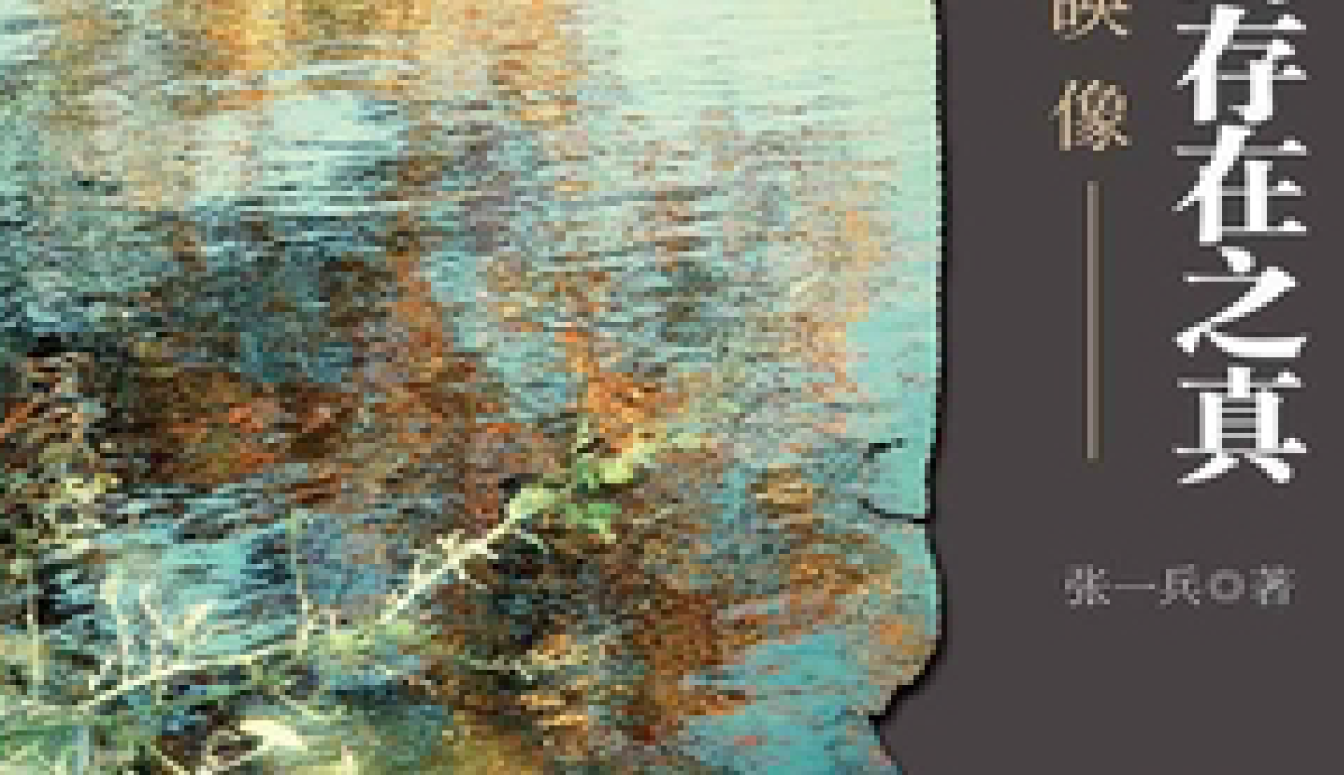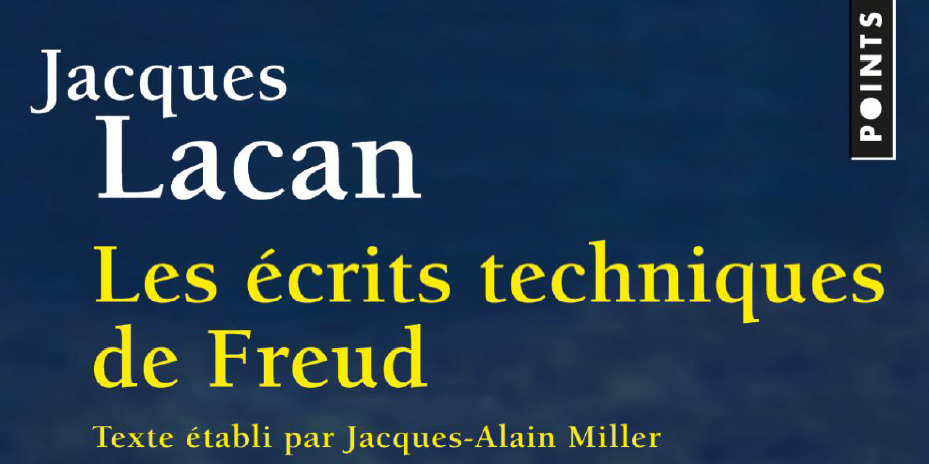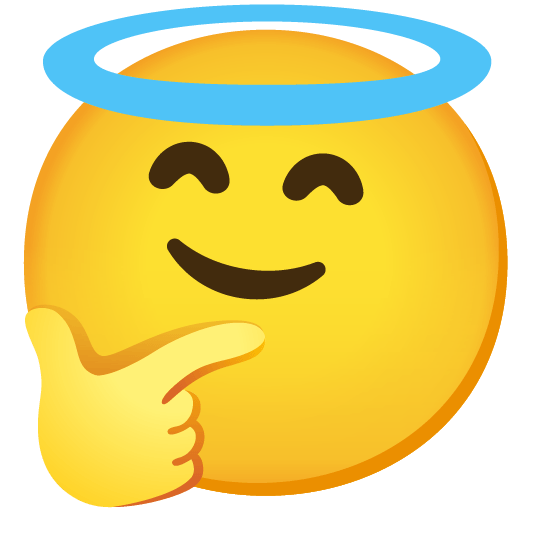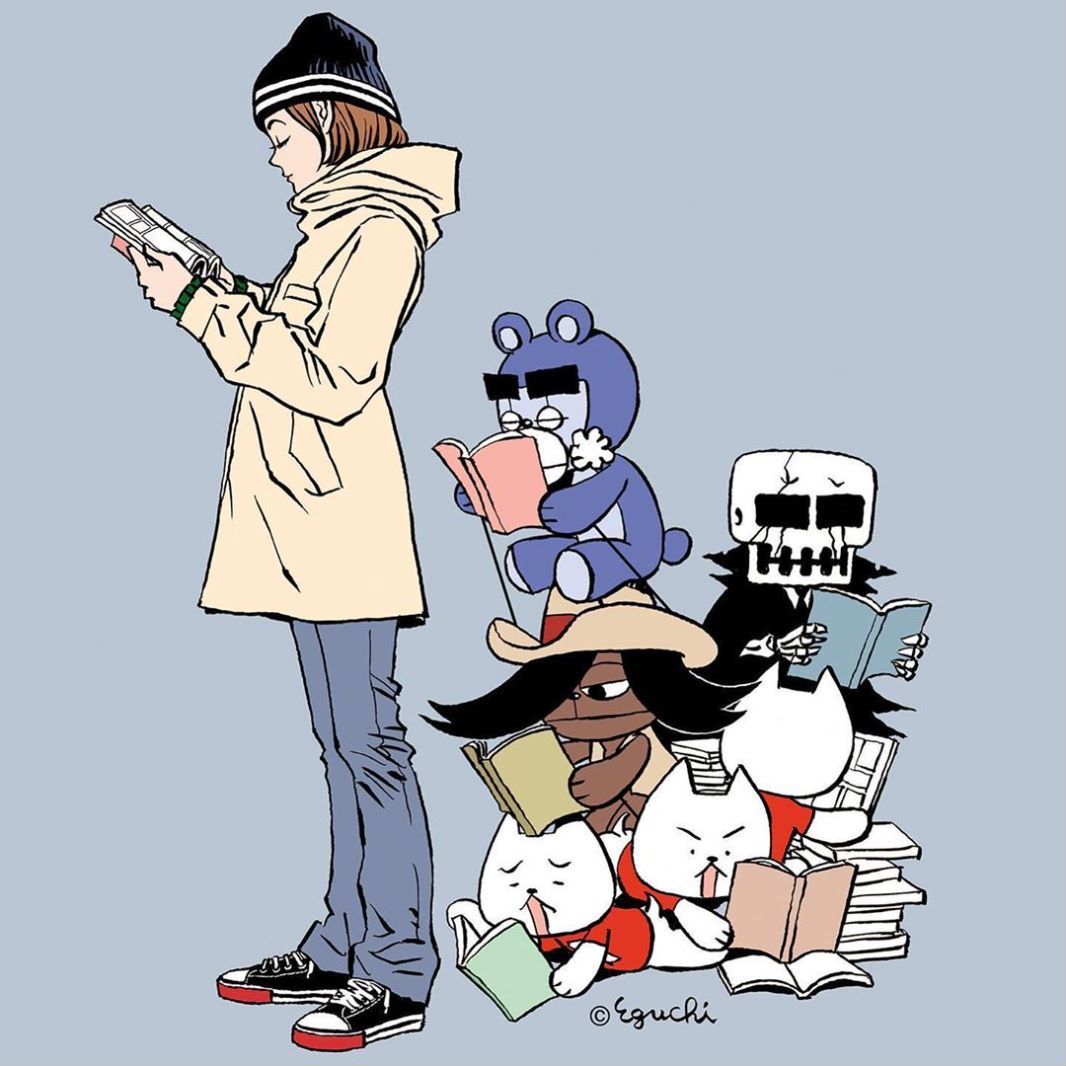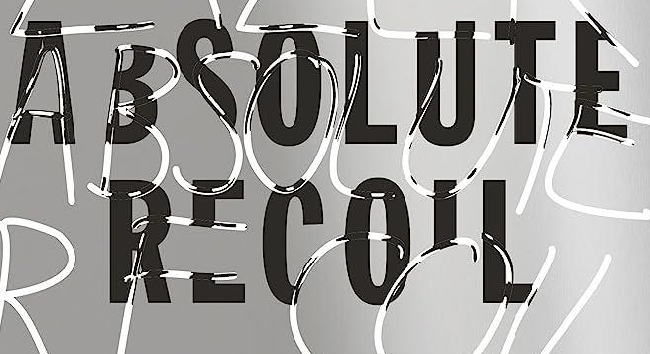note-《绝对反冲》
note-《绝对反冲》
Ivoripuion导言
“毫无疑问这里有块骨头”
列宁引用的恩格斯的主张:唯物主义会随着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而改变其形式。因此对恩格斯唯物主义的修正并非“修正主义”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绝对反冲的概念黑格尔用过一次,在运动中对立的思辨统一下,事物从自己的丧失中涌现。
当设定性被自我扬弃时,本质不再直接由外部的大他者决定,而是通过与其自身他性,以及它同它所涌现而出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复杂集合所决定。
事物是自身内部对自身的绝对反冲。
本书结构:
- 第一部分:对两个具有非先验性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理论(阿尔都塞,巴迪欧)进行批判性分析。
- 第二部分:论述黑格尔式的绝对(AbsoluteAbsolute)。
- 第三部分:黑格尔式的探索,到达超越黑格尔的神秘地带。
旧与新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四个版本:
- 还原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认知主义、新达尔文主义)
- 强烈批判宗教的无神论新浪潮(希钦斯、道金斯等人)
- 话语唯物主义”的任何残余(福柯式的对话语物质实践的分析)
- 德勒兹式的“新唯物主义”:物质=生命=能动自我意识流
弗兰克·鲁达: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
观念论强调了我们身体有限性的同时,努力证明这种有限性如何打开我们无法触及的超越的神圣他者性的深渊。
它们的“本身”难道不是我们思想的终极抽象,是从它们的关系网络中撕裂事物的结果吗?
这句话其实就是辩证法的确定的反思,这也是齐泽克攻击新唯物主义的地方:新唯物主义掩盖了先验和经验断裂,将主观能动性重新纳入自然现实。
对抗泄气的黑格尔
《小逻辑》中三种基本的“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
- 形而上学,即天真的实在论:直接预设了思想的决定和存在的决定的重叠。简单来说就是理性可以得到真理。
- 第二种态度:
- 经验主义怀疑论:它怀疑我们是否能够从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的东西。
- 康德的先验立场:和经验主义怀疑论一样,都不可知论,但是将障碍本身变成了它自己的解决方案:先天认识形式(障碍)成为了我们的认识的范畴。
- 第三种态度:
- 直接或直观的认识:主客体同一性下的绝对超越。辩证思维。
- 没有主张直接直观进入绝对,而是将我们的主体性与其分离的鸿沟转移到原物(the Thing Thing)(绝对)本身中。思辨思维。
近几十年来出现的黑格尔派主要人物最终相当于一个奇怪的达尔文主义黑格尔。
皮平认为的大他者不存在是错的,实则是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大他者是不一致的、自相矛盾的、挫败的,被对立所贯穿,没有任何担保。
(看起来皮平对回溯性构建还不理解)
偶然性和必然性辩证法的核心不在于揭示通过偶然的经验现实表达自己的更深层次的概念必然性,而在于揭示必然性核心的偶然性——不仅是偶然性的必然性,而且是必然性本身的偶然性。
差异
超定是这种自相矛盾的逆转的一个名称,通过这种逆转,一个瞬间将其生长的整体包含在其自身之下。
举个例子:一个生物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与环境的关系是其自我联系的一个功能——主体即实体的感觉很重。
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实体性的前主体的实在,但我们也无法摆脱它。
- 美丽灵魂:是癔症的态度,痛斥世界的邪恶行径,同时也参与其的再生产。
- 心灵法则:是一种精神病态度,即一个自称救世主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内在法则是每个人的法则。
黑格尔就像他自己的所说的骨头一般,是整个后黑格尔传统所抵制的创伤点。
辩证的历史性
典型的黑格尔式解构:孤立分析对象,然后分析他的必然的不一致性,以证明他必然错过了自己发现的关键维度,最后,展示为了公正地实现他的关键突破,人们必须超越他本身。(这也是典型精神分析面对神经症的方法)
辩证过程的黑格尔矩阵是,一个人必须首先在达到目标时失败,因为预期的和解变成了相反的和解,只有在第二刻,当一个人认识到这种失败本身就是成功的形式时,真正的和解才会到来。
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原因来自其内部的充当潜力的障碍——由于其固有的矛盾,生产力动态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社会的经济危机所阻碍。
劳动的异化:劳动不是工人的实现,而是他实现的损失:
工人不是拥有他所生产的,生产的越多,他所拥有的就越少;与其通过生产文明的物体来文明自己,不如说他生产的物品越文明,工人就越野蛮;等等。
紧急避险、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条目,说明了法律的有限性、不一致性,以及法律权利体系本身的“抽象”性质。举个例子,一个不偷东西吃就会饿死的人如果被污名化为没有权利,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法律排除在外,这种拒绝剥夺了主体享有权利的权利——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的权利”。
于是阶级反抗的三段论:
- 当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或无法正常生存时,他或她有权违反法律。
- 在现代社会中,有一整类人,由现有的社会秩序系统地创造,他们的正常生存是不可能的。
- 这个阶级,甚至比个人更应该拥有“苦难的权利”,有权反抗现有的法律秩序。
这个就是典型的毛派:造反有理——这也是真正的主人教训:告诉你什么是可以做的。也就引发了主人悖论:没有主人我们也就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获得自由,也就说,没有主人告诉我们去做“现有的秩序框架内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无法获得所谓的自由——我们不得不以被一位主人强迫或扰乱的方式进入自由。
现在的社会也在似乎让我们“更自由”:比如当我们不能再依赖长期工作,不得不每隔几年寻找一份不稳定的新工作时,我们被告知我们有机会重塑自己,发现自己的创造力。于是自由成为一种负担,我们越没有信息的自由行动,越陷入自由的奴役中,我们需要在一个主人的推动下,从这种来自外部的虚假自由的“教条睡眠”中“唤醒”。
主人的工作方式:他只屈从于自己的欲望,让别人来决定是否追随他,他的权力源于他对自己欲望的忠诚,源于他拒绝在欲望上妥协。
我们总是恐惧死亡,而主人会和你说:那样做吧(你就不会死亡)。
再或者,一种爱式的自由:我自愿去做并非是我不得不去做,而是我对你的爱。这也是基督式的自由——或者我理解是能在式的自由?面对这样的爱,我们能理解自由。但是,这依旧是主人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应该反思:自由不能由仁慈的主人传给我们,而是必须通过艰苦的斗争来赢得吗?
超越先验
走向一种唯物主义理论的主体性
康德与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过程的层次: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遵循仪式,作为物质实践的意识形态;
- 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质询、信仰中认出自身;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教育、宗教、家庭等)通过”物质性实践”来运作,这些机构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这两种层次之间的差距是阿尔都塞承认的,但是齐泽克认为阿尔都塞未能充分把握其内在性质。
举个例子,假装相信/就像他相信那样行动的人,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内在信念。
恋物癖式否认的同义反复“我很清楚……(你爱我)但是我仍然相信(你爱我)”比“我很清楚你不爱我,但我仍然相信你爱我”更加奇怪,因为这里的“但”的转折表现了一个分裂——同义反复,为什么God is God。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分裂,本质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知识必须被信仰补充?
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承认知识无能,因为知识本身内在的分裂和差距。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的工人清楚知道资本主义剥削(知识)但是依旧是在努力工作(信仰),如果没有这种信仰的补充,知识本身无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阿尔都塞只能见到指出这种分裂,但是齐泽克会指出:工人在知识层面上知道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但这个知识本身并不完整,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仍然会认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全能必然会退化为“全在潜能”,正如公共社会中,不被执行的暴力机构才是最有威慑力的,被视为 全能 的父亲只有在他的权力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永远未实现的威胁时,才能保持在这个位置。
也就像64时期,当坦克真的碾压过人群时,依赖于暴力的政府反而失去了其威慑力。信仰可以弥补知识的内部裂隙。
我们不仅要在“存在决定意识”的上主张唯物主义,还要更进一步,要考虑维持意识形态的物质(意识形态)机构,甚至包括观念秩序本身的内在物质性(大他者)。
小时候老师善意的谎言:“将来可能成为数学家,他能当作家..”就体现了语言内在的不一致性:表面的谎言(违反规范)导致了实际的规范实现(学生成功)。
阿尔都塞的质询中,警察的质询的影响在于无知的罪恶感:在权力看来,我原本就有可怕的罪恶感,尽管我不可能知道具体是什么,因此我更加有罪或者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在这种无知中我真正有罪——主体不知道大他者想要什么——Che vuoi?
而罪恶感的主体其实就是象征认同之前的主体:一个淫秽的、无法穿透的、没有身份认同的质询的中间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