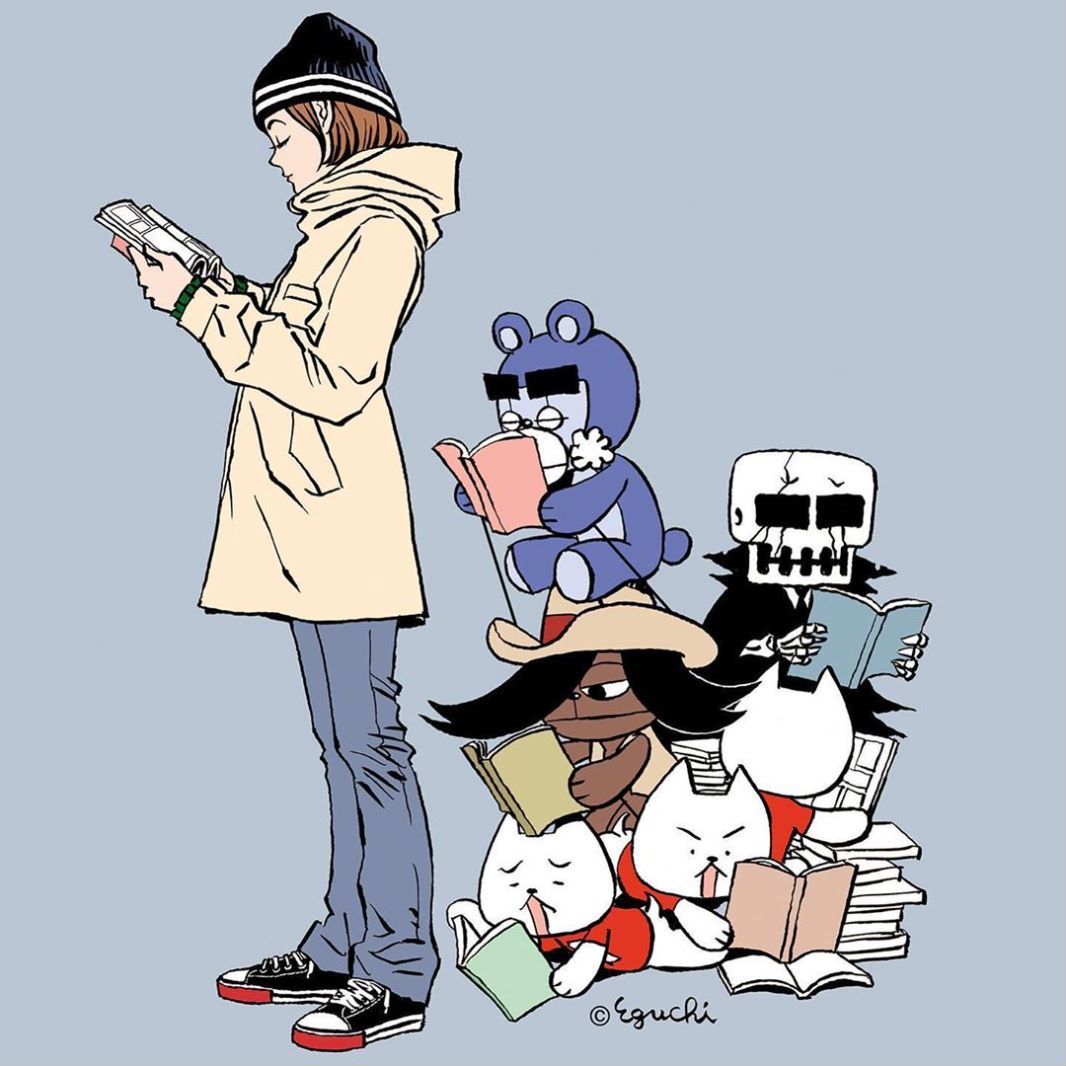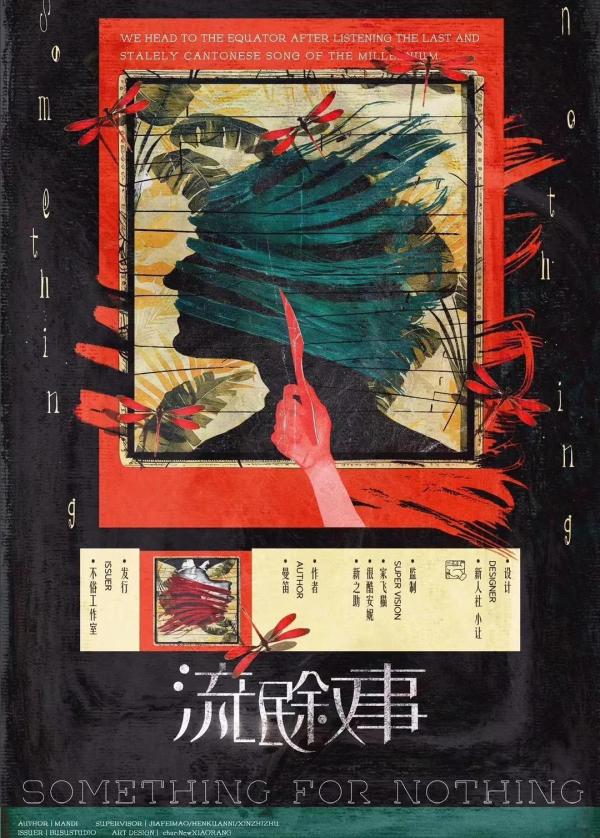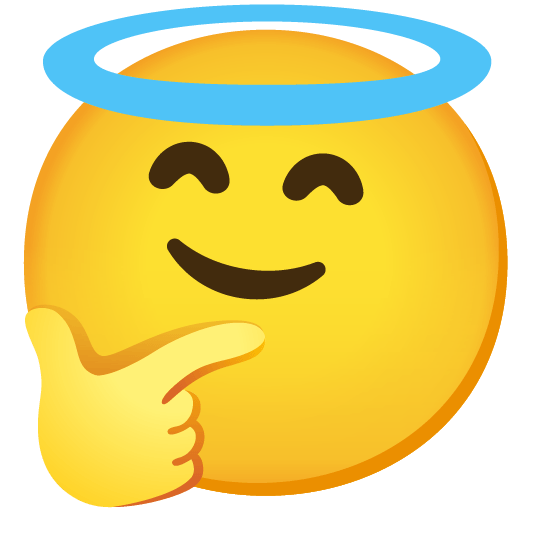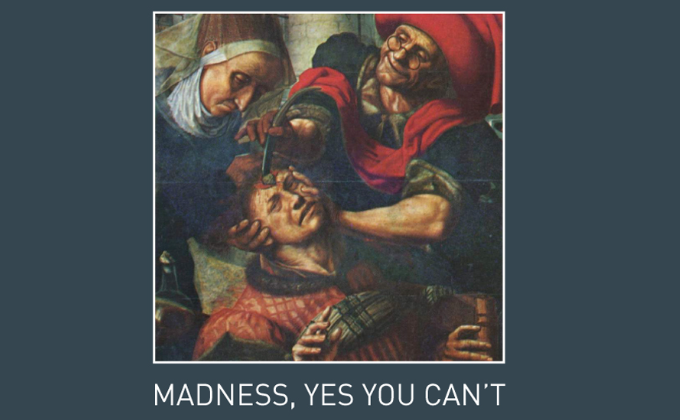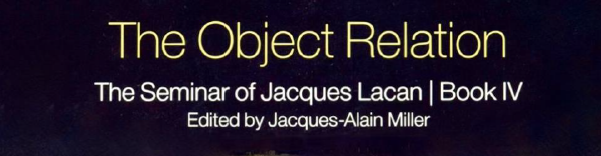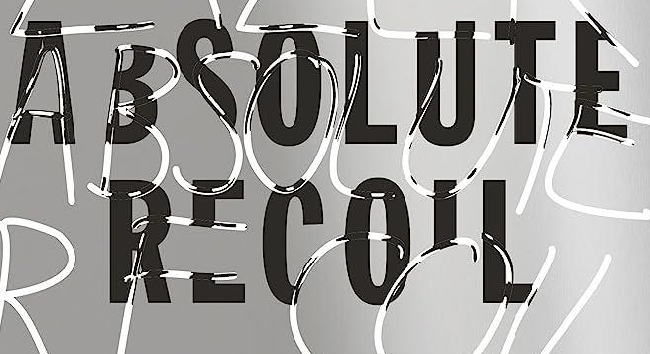聊聊杨景媛一事
聊聊杨景媛一事
Ivoripuion对杨景媛事件的主要批判会将其包装为“辱女狂欢”,批判者们认为在法律和规范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对女性侮辱的秘辛,并通过假设“想必侮辱”的男性“主动式被动”地陷入同样的“侮辱”之中——批判者幻想中的男性网民,因为主动享受着倒错式的集体意淫而被动完成了辱女行为。在这悖论性的批判之下,幻想通过“辱女”这个主人能指化的伪造地基建造起整个叙事高楼,试图将学术不端、亲人离世、污蔑控诉等所有的创伤吞噬——毕竟,还有什么比将一切苦难都转译为性别叙事,更能完美遮蔽父姓机器无能的哀嚎?当遮蔽完成,象征秩序便再一次完成了系统升级,批判者成为了真正辱女者——自然也是最忠诚的父权主义者。
杨景媛事件是破碎的:伪造《离婚法》的学术欺诈、将“湿疹”误认为是性骚扰、败诉后对肖同学“追杀到天涯海角”的宣言等都是偶然突发的。但是当伪女权主义者将这些事件缝合到“父权压迫女性”的宏大叙事时,真实而突兀的事件被回溯性异化为连贯的历史,杨景媛事件也因此产生了其同一性的“自我”——“辱女狂欢”。而武汉大学的沉默、相关人员的上门警告等接连发生,更是将破碎的历史在主人话语进一步弥合,产生了其“自我理想”,杨景媛事件成为被父姓机器肯定的“厌女症”下的癔症癫痫。
这种叙事缝合的核心动力,在于将事件中所有令人不安的“例外”——伪造、误认、过度追索、司法结果与其宣称的“迫害”强度间的裂隙整合为“性别对立”的逻辑中,将学术诚信的崩坏、个体精神状态的极端化、法律程序的实际效能、机构责任的模糊化等需要提问并探究的问题全部避开,将需要严肃对待的阶级矛盾转移娱乐化:“性别对立”何尝不是一种奶头乐呢?毕竟当人们纠结于“性别对立”的激烈矛盾时,就不会去在意逻辑性别本身到底是否存在了。整个事件中的肖同学/杨景媛都成了“性别”合理化所必须的“外部入侵者”,人们将他们排除来实现性别的逻辑完备。
批判者们将杨景媛视为“厌女狂欢”的受害者的思考正如一个自我抱怨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总是在叹息自己一生都是在默默受苦、牺牲,但是这里的“默默受苦、牺牲”正是她的想象性认同,是她自我同一性的基础。换言之,家庭主妇可以牺牲一切,但是不能牺牲牺牲这件事情——杨景媛可以牺牲自己成为“厌女狂欢”的受害者,但是不能牺牲自己放在性别话语中“女性”的身份!所有的批判者们都如自我抱怨的家庭主妇认同的家庭网络下的主体性空间般认同父姓符号系统下的逻辑性别本身。
最终,这种批判话语完成了一场精妙的权力置换。它表面上声讨父权,实则通过将“性别压迫”确立为唯一有效的解释框架和斗争场域,不自觉地强化了父姓机器的绝对权威。它将所有社会矛盾、个体悲剧、制度缺陷都收编、压缩、转译为性别问题,恰恰宣告了父姓秩序的不可撼动——仿佛除了在这个它划定的擂台上搏斗,人类再无其他值得言说的痛苦与反抗。批判者愤怒地指向的“辱女者”,在批判者自身的话语实践中,反而被降格为父姓结构无意识运作的被动道具;而批判者自身,则在挥舞“性别批判”这柄看似锋利实则由父权自身材质锻造的利刃时,成为了父姓象征秩序最完美的守卫者——他们以反父权的名义,勤勉地清扫着任何可能动摇父权逻辑根基的、溢出性别范畴的“噪音”与“例外”,确保系统的叙事闭环且光滑无瑕。
所谓的“辱女狂欢”,不过是父权主义者们再一次观念论的便秘:他们以为通过性别叙事就可以吞下所有的创伤,却不知被强行压入食道的实在界结石早已经将整个逻辑的肠道塞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