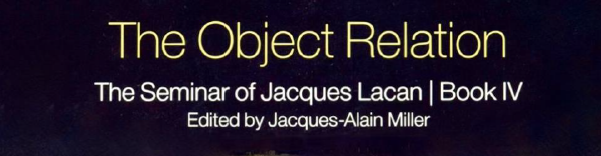聊聊性自由
聊聊性自由
Ivoripuion从“性压抑”到“性自由”,“性”这个词语本身似乎早已化身为一个主人能指——通过预设一个空洞的、无根的能指,来获得一系列的后续有关“性”的知识,当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性自由”呐喊、为“性压抑”感伤之时,“性”本身的知识却早已被忽略,成为了那个通过遮蔽自身而支撑起整个知识大厦的伪地基。“性”——这个隐秘的主人能指,以“自由”或“压抑”的辩证法为幌子,将人们的意向转移:它将性不存在的创伤转化为被象征化的符号对抗,让人们在“解放”与“压迫”的虚假战场上厮杀,却对真正的目标视而不见——那个永远滑脱于能指链之外的、作为创伤性内核的性本身。
关于“性自由”的争辩往往是如下的对立:
- “性自由”是“丧权辱国”的行为,我们应该对其进行道德批判。
- “性自由”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是文明进步的体现,我们应该对其进行鼓励。
对于以上的争辩,人们的选择往往是择其一站队而反驳另一方,但我们不妨认为二者观点皆是正确的——即在符号系统的背景下,看似一正一反的两个观点被恰当的置于了莫比乌斯环的一面上:前者将性器官转化为同一性的隐喻边疆,后者将性的快感包装成性市场的流通货币,两者都默认了身体必须承载某种符号意义。
人们通过假装有一个“有意义”的身体而回溯性地能指化出“完整的”身体,这个身体被嵌入符号系统,产生了使用价值,身体的拥有者则对身体产生了使用权,争论就此展开:“她是否有权如此使用身体?”这种在身体彻底符号化预设的基础上的争论,并非当代独有,其极端形态早在萨德的思想中就已裸露出来:
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人生而自由,那么人不得拥有和奴役他人,也就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一个男人不能拥有独占任何一个女人,而相对的一个女人也不会独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也就不能以爱上其他人或者结婚为由拒绝另一个男人的求爱。人生而平等,那么所有人虽然不能有“拥有权”,但是却可以平等的拥有“享用权”,因为他是所有人共同的财产。那么“所有男人对所有女人都拥有平等的享用权”,也就是虽然不能拥有女性,但是可以享用她,同样的,无关乎性别的,所有人彼此间都有平等的“享用权”。
萨德的逻辑,以其极端的形式,暴露了“自由”与“平等”在符号系统中的实质——一种将身体彻底客体化、公共化的“享用权”经济学。这种“平等享用权”的构想,恰恰是符号系统吞噬真实身体的最赤裸裸的证明:它表面上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骨子里却将鲜活的人体彻底降格(同时也是崇高化)为无差别的、可供流通交换的符号性货币,一种抽象化的、祛除了全部独特性和内在深度的“财产”。在这里,“自由”不再是通向个体存在与欲望实现的路径,反而成为符号系统完成其抽象化、均质化运作的完美借口。
在我们当下讨论“性自由”时,也恰恰落入了如萨德揭示的陷阱中。“性自由”被倒错式地商品化、公开化,人们需要精心挑选满足“性自由”法则的事件、事物来完成“性自由”的仪式,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将身体更深地嵌入资本主义预置的符号系统中。
在争论的双方参与到戏剧中后,“性自由”闹剧的实现往往需要第三方协助才能形成完整的三元组:
- 保守派:认为惩罚“性自由”实践者能够维护国族尊严。
- 自由派:认为“性自由”实践者的选择彰显了免受父权凝视操控的主体性。
- 公众:通过围观保守方VS自由派的对抗,假定了想必“相信保守”和想必“相信自由”的主体间对抗。
公众们通过幻想出来的想必相信的主体而“主动式被动”地同样陷入了“相信”中,同样地拒绝了身体本身发出的实在界哀嚎、拒绝了“性”本身的不可能,认可了大他者对身体的符号化、认可了父权带来的倒错式快感。
“性自由”当然带来的并非所谓的“自由”,而是更加彻底的规训。身体被彻底地功能化、商品化,成为符号价值流通与增值的一般等价物。快感不再与个体独特的欲望/求知欲相连,而是被“性自由”的符号收编,成为一种需要符合特定规范、可供展示和评估的“正确快感”。我们越是激烈地争论“自由”的边界,越是虔诚地践行“自由”的仪式,身体便被规训得越深,离那个无法被言说、无法被象征化的“性”的创伤内核也就越远。
一切争论的终点,不过是依赖父权制(当然也是阳具中心、逻各斯中心、资本主义)建构的符号系统又一次精妙的自我确认:我们总归是父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