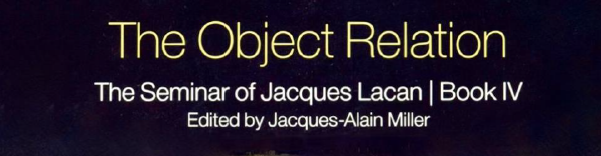厌男:被误读的欲望幻象;厌女:象征秩序的暴力排泄
厌男:被误读的欲望幻象;厌女:象征秩序的暴力排泄
Ivoripuion庸俗的女权主义者往往会在厌女、厌男的问题上陷入二元对立框架:
- 厌男:对男性个体的情绪反应;
- 厌女:对父权制结构不公的证明;
这种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二元对立——将厌男贬斥为“无害情绪”、将厌女升华为“结构性不公”的操作,恰恰体现了父性象征秩序的自我合理化功能,父权在此完成了一次诡异的自我辩解:它通过将压迫“客观化”完成了对其暴力本质的消毒。
本文将对这种庸俗二元论进行批判,试图揭露:厌男是结构性矛盾的转移,厌女则是父权暴力为掩盖自身的“无根性”、保障自身稳定性而实施的排泄仪式。二者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如莫比乌斯环的两面,最终在一个拓扑平面相交。
有关厌男
关于厌男的陈词滥调往往将厌男简化,将其描述为对“单个男性或者男性群体的情绪化体验”,并以此为地基构建起空洞歪斜的高楼。要推翻这层意识形态幻象,首先我们需要对这种论断进行现象学直观。
将“厌男”的作为反应的情绪一笔带过的行为,恰恰是对此在生存论层次结构的暴力切割。当把作为此在展开的现身情态降格为心理附属物时,已深陷传统形而上学的认知陷阱——海德格尔所批判的“现成在手”的思维方式,情绪在此被僵化为可观测的对象性存在。在这种常人化的认识论框架里,此在及其展开变成了固着的、孤立的结构——产生厌男情绪的个体不在是以共在的形式操心,而是简单化为一种被剥离具体历史场景(正如癔症结构往往是在场景-情绪的分裂中选择情绪的一方)的癔症式质问——“男人究竟想要什么”,也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会说出自己怀有“厌男”情绪的人往往是女性特质的人,这种永恒的能指追逐,实则是对父权制大他者欲望的镜像投射。“癔症式”的“厌男”成为了维持象征秩序动态平衡的装置:通过不断制造怨恨情绪巩固大他者对象征界的统治。
“单个男性或者男性群体”的含义也值得玩味。当“厌男”者将否定投射向具体的男性时,攻击的不再是父权制本身,而是符号系统制造的镜像替身——那个“坏男人”的个体。当女性痛斥某个职场性骚扰者时,符号系统已经完成了双重的暗箱操作:一方面法律允许有限度的道德批判,另一方面将矛头从“父性秩序”()转向了“道德败坏个体”,这就如同资本主义允许人们咒骂“肮脏的企业家”,但是禁止人们谈论制度本身。父权制不断地生产“普信男”、“性侵犯”等能指反派,以构建“好男人”形象来维护“性别规范”的合法性。同时,资本主义再生产将对男性个体/群体的情绪加工为标准化可以被象征界吸收的能指符号,使批判沦为符号消费的娱乐商品。
于是,将“厌男情绪”简化为“对单个男性或者男性群体的情绪化体验”,实则时大他者最成功的一次意识形态操作:
- 忽略实际的历史场景,将否定及否定者孤立化。
- 制造局部敌人转移系统性矛盾。
- 通过生产道德审判、娱乐符号提供代偿性满足。
- 永恒轮回的阴影在此显现:大他者不断持续地生产以及象征秩序扩张。
有关厌女
关于“厌女”常见的论断来自于凯特·米利特的观点:“性别歧视”通过“男女天生差异”的意识形态为父性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厌女”是父权制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规训和执行父权制规范的工具。
这种看法依旧不自觉地复制了父权制的运作逻辑:通过理性辩护(性别歧视)和非理性暴力(厌女)掩盖了二者共同服务的死亡冲动——父权制为逃避自身不可能性(无法真正统合性别差异却又要追求“太一”)而进行的自我再生产。“性别歧视”和“厌女”实则是同一压迫结构的双重表达:
- 性别歧视是象征界的缝合,通过生物决定论掩盖父权制的匮乏:它无法为象征界提供真正的本体论依据。
- 厌女则是实在界创伤的返回,当缝合点出现了纰漏,癔症结构发出癔症式哀嚎,象征系统便以暴力将其制服,但这种暴力恰恰体现了符号系统的脆弱性。
女性主义者也在此陷入了父性秩序的囚笼:对厌女的批判再一次沦为了父性秩序升级的燃料。比如女性主义者在凯特·米利特之流的基础上批判往往会将一些“厌女”的语言标签视作一直女性情感表达和行为,并进一步巩固性别刻板印象,而实际上当女性被唤作“疯女人”的时候,大他者的诡计就已经显现出来:通过能指固着的方式依旧肯定了女性的存在,并进一步将其作为例外肯定了整个“男-女”结构出来的象征系统的合法性。而另一面,当女性主义者将”厌女”等同于”父权制的证明”时,遮蔽了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结构性位置。这种认知范式使批判沦为对既定秩序的镜像复制:通过不断命名”厌女”现象来确认父权制存在的”真实性”,而这种确认本身恰是对大他者欲望的臣服。
当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已发展出精密的符号转换机制。当社交媒体上”女性独立宣言”被制作成粉色字体的短视频,当”厌女”批判被包装成畅销书封面的烫金标题,象征秩序完成了对反抗的收编——那些本应撕裂符号系统的批判性话语,最终被转化为维持系统运转的润滑剂。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澄清“厌女”实则是“父权暴力为逃避不可能的可能性的一次排泄仪式”:父权制通过周期性地制造厌女事件(从猎巫运动到荡妇羞辱),将自身无法消化的创伤性残余(性别差异带来的本体论焦虑)以暴力方式排出系统之外。这种排泄具有双重功能:既通过排除异质性能量维持系统稳定,又通过制造排泄物的可见性(如网络暴力中的女性羞辱)反向确认系统”洁净性”。正如巴塔耶所言,排泄物的肮脏恰恰证明了消化系统的完整。
拓扑学褶皱处的相遇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莫比乌斯环的拓扑结构时会发现,所谓”厌男”与”厌女”的二元对立实为视觉幻象。在象征界的褶皱处,两种现象共享着相同的生成逻辑:
- 剩余快感的循环:厌男情绪通过消费主义转化为”女性向”文化产品(如乙女游戏中的完美男主),厌女暴力通过道德审判转化为集体宣泄的狂欢。二者都在生产象征秩序的剩余快感,维持欲望机器的运转。
- 他者化的辩证法:厌男话语将男性他者化为可憎/可爱的客体,厌女实践将女性他者化为可弃/可欲的客体。这种双重他者化构成了拉康所谓的”非全逻辑”,确保没有任何主体能完全占据符号位置。
- 创伤的转译机制:二者都是对原初创伤(性别差异象征化的不可能性)的防御性反应。厌男是癔症结构对象征菲勒斯缺失的过度补偿,厌女是强迫症结构对母性身体威胁的驱魔仪式。
这种拓扑学透视揭示了更深层的运作机制:当代父权制已进化为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智能系统。它通过制造对立面的假象(厌男VS厌女),诱导反抗者陷入永无止境的镜像战争,而系统本身则在矛盾双方的相互消耗中完成升级。就像病毒不断变异引发抗体内战,最终耗竭宿主免疫系统。
可能的出路
要突破这个永恒轮回式的对抗,“穿越幻象”作为精神分析结束的第一步兴许是不错的选择——不再寻找”更好的性别理论”,而是直面象征系统的根本不可能性。这种行动包含三个维度:
- 症状的忠诚:停止将厌男/厌女视为需要矫正的”错误”,转而将其视作揭示系统裂缝的症状。就像精神分析师倾听患者的口误,我们需要倾听这些”错误”指向的实在界创伤。
- 否定的实践:借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拒绝认同任何性别范畴的同时,保持对范畴化暴力永不妥协的批判。这要求我们既在象征界内部作战,又时刻准备跳出符号秩序。
- 伦理学的悬置:真正的伦理行动发生在象征秩序崩塌的瞬间。当女性不再质问”男人想要什么”,当男性停止表演”男子气概”,或许我们会触摸到那个超越性别矩阵的”实在界的微光”。
这个出路注定是悲壮的,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任何对父权制的实质性挑战都会遭遇象征系统最猛烈的反扑。但正如拉康所说,主体性正是在与大他者的致命博弈中诞生的——或许只有当我们停止寻找”正确的性别政治”,转而拥抱那个永远无法被象征化的性别差异实在界深渊,才能开启真正的解放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