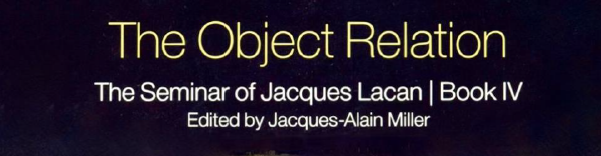作为后现代艳舞的《独上C楼》
作为后现代艳舞的《独上C楼》
Ivoripuion《独上C楼》以爵士、嘻哈的风格描绘了男女爱而不得后的独自起舞的情景,这种爱而不得并非是短暂的别离而是性关系的不存在。正如神经症中折磨女性的问题往往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折磨男人的问题往往是“我是死了还是活着?”,性关系的问题就是存在问题,看待性关系的方式也正是死亡观。《独上C楼》因此以一种戏虐、欢乐的方式传递了面对根本无意义的态度:我虽知道了这一切的荒诞,但是我依旧要在荒诞中狂欢,以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情绪直视令我痛苦的欲望、以悲剧精神解决悲观主义。
《独上C楼》的歌词采用了大量的重构的手法,将“诺亚方舟”、Bohemian Rhapsody的歌词“little high little low”等元素捣碎揉进《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的故事背景,以文本本身荒诞的偶然性表现了性关系不存在的必然性,这也是很多文学作品中惯用的技俩,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艾柯对《哈姆雷特》的解析,他没有结构《哈姆雷特》的同一性,相反他将其重新建构,而重构的同一性是基于一系列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结果1。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独上C楼》没有用解构的力量来破坏《独上层楼》的肯定的连续性,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否定力量的自我指涉结果的《独上层楼》的肯定性:性化是不可能的,但也因此我们需要爱情。
爱情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想。正如意识形态掩盖了实在界阶级斗争的象征化失败,爱情同样掩盖了性化的失败2。性化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等你等到白了头”、“只要你点头,我就扶你过马路”这样的祈求,实则是一种哀嚎,这样的哀嚎是大他者透过神经症的主体发出来的。活生生的肉体在象征界无力交缠而生产出性欲——一个作为神经症永恒无法填补的空洞,在性欲这样空洞的地基上,爱情可以以隐喻的形式来“试图”弥合这个空缺,就如“扶你过马路”其实是站在对方立场来进行的“被爱者”和“施爱者”的隐喻式的立场转换。
构成后现代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目的论世界观的消失,放在这里实则就是“你永远也不会点头”。通常的,现实主义重视“理想模式”,现代主义重视“象征模式”,后现代主义则是重视“平面模式”3。“现实主义”面对爱情掩盖的不可能总会寻求下一个完满的可能性,“现代主义”则会颓废忧郁,“后现代主义”则是拥抱爱情、拥抱不可能,因为不可能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边界带来了可能性——在此,存在主义的亮光透了进来。你永远也不会点头,你若是点了头,扶你过马路的我就不会再要求你点头,因为欲望总是指向了别的地方。
《独上C楼》最终以独自起舞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掩盖的不可能性的哀悼。歌曲中的歌者在对唱却永远无法回应彼此,他们以产生剩余的声音构成了象征界的空洞——语言的空洞,透过语言这种形式,他们永远无法了解彼此。“你独上了西楼,完全不想回头”,但也正是“你的离开”构成了《后现代独白》,在你的独白里,我独自起舞。
我要如何爱你,让我尝试细数:
我爱你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广,
我爱你的本我,自我,超我直到其最深远之所至,
你的躯体,灵魂,心脏,思想与精神,
你的理想,幻觉,欲望与冲动。
1: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2: 《导读齐泽克》
3: 《后现代交锋丛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