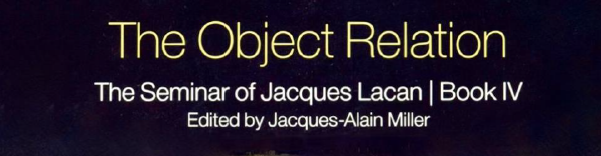河边的原乐
河边的原乐
Ivoripuion从超我的二重性中我们不难推导出一个所谓和谐稳定的社会向来预设了一个能毁灭一切的原初凶手,这也是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及的原初父亲——这样一个前神话中的享有原乐的父亲没有经过阉割而能享用所有的女性。摒弃掉超我中种系发生神话的向度重新解读未经过阉割的原父后,不难得出除权弃绝后拒绝象征化的精神病就是可以承载人们对于原初幻想的角色。
纵览全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谁是真正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无论是无需理由就可以杀人的精神病结构的疯子还是家中摆设温暖的神经症结构的许亮,都没有确定的线索确定他就是凶手,直到许亮跳楼自杀,担任侦探角色的马哲才肯定凶手就是疯子。这样一个幽灵般的凶手正是任何一个看似和谐统一的逻辑基础——充满暴虐、没有秩序却又能享受到过度原乐的原初父亲,杀死对立的原初父亲才有可能得到现有的和谐稳定社会。当主体认同现行的社会秩序这样一个权威的父亲,也就变相认同了那个原父。
余华在很早就洞见了现行可靠的社会秩序背后的真实是无法抵达的,任何一套现行的社会秩序总是扬弃掉对立面结构的: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
余华 《虚伪的作品》
“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正指明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宇集合的有限性,它排除了原父及其享用的原乐进入稳定持续的欲望经济,但是处于集合边界的混乱的实在总是在指示着这个宇集合的根本匮乏。面对象征界匮乏带来的写作束缚,以及为了避免在经验下的作品总是本雅明所谓的“生理学”,余华采取了一种“虚伪”的方式,即通过想象的中介来努力接近真实的原乐——具体的说是想象界和实在界作用的他者原乐,这样的“虚伪”带来了《河边的错误》这个作品。
文章多次出现的意象是鹅群,不妨将鹅群看作符号化的人群,便可以很自然的得出马哲在小孩被杀后想象鹅群得到平静的原因:面对死亡的真实,只有成为符号化的常人里才能隐匿自身。相对的,开篇么四婆婆赶鹅时那一只游离在鹅群之外的调皮小鹅就可以类比为没有完全接受象征秩序的人,结合上下文来看,小鹅实则就是疯子这样一个精神病结构的缩影。小鹅能不听么四婆婆的召唤而如风筝般自由地嬉戏,正如人们幻想中疯子能无视法则的律令而随意的杀人,这两者都因为不受父之名的束缚而能享受到过度的原乐。
作者将疯子这个形象描绘为人们幻想的享有过度原乐、混乱的原初父亲在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出:
- 与么四婆婆的乱伦:这里的描写比较隐晦,可以从与后期么四婆婆响亮的求饶声形成鲜明对比的前期很轻的呻吟声、无论什么时候么四婆婆都不会开门推测出。么四婆婆将疯子看作自己的丈夫,没有担负起象征父亲的角色,这就导致了疯子的除权弃绝。
- 疯子总是在河边洗衣服:河边作为接二连三地发生凶杀案让人直面实在的场所,疯子却可以若无其事地在那里做洗衣服这样一个稀松平常又惹人遐想的事情,这是不是说明疯子有什么比“正常人”多出来的什么东西?也正是这种多出来的权力让疯子可以享用过度的原乐。
- 一个人看到马哲没有看到疯子却惊呼“那疯子又回来了”:这正是对幽灵般原父的描写,人们幻想的原父并不需要一个实际的对象,只需要有这么一个代表破坏的人作为秩序的对立面。
文章结尾,马哲枪毙了疯子,这代表着马哲意识到了疯子代表的对立面是象征秩序无法接纳的,而他身为象征秩序的守护者不得不杀掉这个原初父亲。接下来,在局长和妻子的压力以及医生的询问中,马哲彻底发现了象征秩序的匮乏,从强迫症结构转化为了癔症结构。从强迫症结构转化为癔症结构,也符合了马哲辨证发展的规律,但是关于“合题”作者并没有明确给出。最终在“真有意思呵”这样一个戏谑性的话语中,发现了河边的原乐的马哲奔向了意为“合题”的穿越幻想。